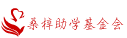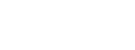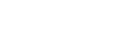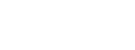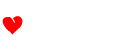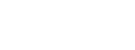伯伯的教诲与我的知青生活
2014-03-11 阅读:115842次
周秉建

我们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生的人,在上个世纪60年代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有2000万左右的老三届及其他后几届的学生都成了“知青”,成为在当时特殊历史环境下造就的一个特殊群体。
我是1968年8月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到内蒙古大草原插队的。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中,学校早已“停课闹革命”并且实行了军训管理。从1967年开始按照上级有关指示精神,逐步动员组织毕业生去兵团或下农村。学校里有很多同学都报名上山下乡,有去东北兵团的,有去山西的,也有要求到内蒙古的。那时的口号是,毕业生要“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学校只负责分配66届的初中、高中毕业生,但是也允许67届的毕业生报名,而68届的毕业生一个也不要。可是我下了决心,一定要到内蒙古的牧区去插队落户。自己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并不断坚定自己的意志。因为怕得不到批准,我便一次次地写申请,一次次地找学校和军训的负责人,找西城区安置办的同志和内蒙古来北京招收知青的工作人员泡蘑菇,几个月后终于获得了批准,同意接收我到内蒙锡林郭勒盟的阿巴嘎旗安家落户。而直到这时候我才把消息告诉了伯伯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
伯母虽然通知我在临行前的任何一天下午都可以去西花厅,但我还是在妈妈的帮助下,在做好了行装的一切准备之后,在离开北京的前夜才去向伯伯和伯母两位老人家辞行的。
8月6日下午到,西花厅的院子里很安静。虽然从红墙外天空中不断地传来造反派的喧嚣声,可是伯伯依然在办公室里有条不紊、繁忙地工作着。我先见到伯母,她很高兴我的到来,我们在客厅边交谈边等着伯伯“下班”。由于伯母已经知道我要去的是边疆民族地区,就特意给我讲了当年红军长征经过彝族地区时,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共同结盟的故事,并且叮嘱我要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要和他们团结友爱。
快到晚饭时,伯伯才从办公室里走出来。他见到我非常高兴,用他温暖的大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热情地鼓励我说:“秉建,我坚决支持你到内蒙古大草原安家落户,走毛主席指引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是我从小长大第一次听到伯伯不叫小名而称呼我的学名,心里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噢,伯伯这是在和我谈话,我已经长大了”这样的感觉。他还关切地问我:“你到内蒙古的牧区去,做好思想准备了吗?要多想些困难,想得太简单了,遇到困难就容易发生动摇,要做好战胜各种困难的思想准备。”他还问到我吃不吃牛羊肉?因为我只吃牛肉,不吃羊肉,就如实地做了回答。伯伯听了马上嘱咐我:“不要忽视困难。你过去不吃羊肉,到了牧区你还要锻炼吃羊肉,首先要过好生活关,这个很重要。你去的是牧区,是少数民族地区,要注意和尊重那里的风俗习惯。”伯伯边说边把我领到一幅大型全国地图的前面,向我仔细询问了我将要去的内蒙古牧区所属的盟、旗的具体名称,当时我自己还真的不大清楚锡林郭勒盟和阿巴嘎旗的确切位置,可当我一说出这个地名,伯伯立刻就找到了,还边指着地图边告诉我:“你去的锡林郭勒盟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个盟,旗相当于内地的县。生产是以牧业为主的,气候和环境都比较恶劣,它的北部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有些情况还很复杂…… 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面有三个盟,西面有三个盟,现在暂时划到了临近的省份,但以后总还是要归还到内蒙古自治区的。”我当时还不大懂得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伯伯讲得这些话我都记住了。
吃晚饭的时候,伯伯有些歉意地说,“没有什么好招待你的,最好的支持是精神上的,你说对吗?”这时伯母在一旁告诉我,这是伯伯特意在为你饯行呢!实际上,两位老人家的饭菜很简单,只有两菜一汤,因为我才添加了两个菜。饭桌上有一盘翠绿的青菜,我既没吃过也没有见过,心里正在琢磨呢,就见伯伯指着这盘蔬菜高兴地给我介绍说,“今天我请你吃毛主席的家乡菜苦瓜,很好吃的。”当我把苦瓜吃到嘴里,的确尝到了苦涩的滋味儿,但是更感到了伯伯的良苦用心。自己暗暗地下决心,到了草原,一定要不怕困难不怕吃苦,不能辜负伯伯的期望,要用实际行动让他放心。伯伯一边吃饭,一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们要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把你们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自己也还要活到老、学到老,跟毛主席革命到老……”吃饭的时间过得很快,饭后伯伯又要去工作了,他再一次握住我的手嘱咐说,“你到内蒙古牧区安家落户,一定要到贫下中牧中间去,一定要虚心向那里的劳动人民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一定要和蒙古族人民搞好团结,做贫下中牧的好女儿,安心干革命。”伯母随后也把他们老两口准备好的一套《毛泽东选集》和一些毛主席像章作为礼物送给了我。她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你们是属于党、属于人民的,我们要把你们教育成为劳动人民的后代。你要到社会中去经风雨、见世面,到阶级斗争中去锻炼自己,到工农兵中去改造自己。他们是你的老师,要向他们学习,不要靠我们,要靠毛泽东思想,靠群众、靠自己。最后还说,“送你一条你伯伯很喜欢的毛主席语录:不但要有革命热忱,而且要有实际精神。你也要像伯伯一样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说到做到不放空炮。要把革命热情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坚持与工农相结合,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前进。”
就这样,第二天,1968年的8月7日,我满怀豪情、带着学校师生们的期望和亲人的嘱托,高高兴兴地离开了首都北京,奔赴内蒙古大草原,与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一样,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和很多知青不一样的是,我一直都没有哭。
我下乡插队的地点是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的新宝力格大队。刚去的时候什么都不会,不要说干牧业活儿,就连吃饭、睡觉、说话都需要学习。牧民们待我们知青非常热情,就像是对待自己的孩子或兄弟姐妹,他们手把手地教我们学习骑马、放牧、接羔、做饭、挤奶和做针线活儿等等,还不厌其烦地教我们学习蒙古话和简单的文字,当发现我们的缺点或不足时,也会及时给予帮助。在贫下中牧的教育和帮助下,自己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进步,劳动的本领有了很大的提高,身体也锻炼得更加健康强壮,我的脸已经晒得黑红黑红,我的心也被锤炼得更加坚定,意志也更加坚强。每当伯伯和伯母在北京收到我从草原寄去的信件,无论工作多么紧张和忙碌,他们都要抽出时间来,通过家信了解我在牧区的生产生活情况。当伯伯看到我身穿蒙古袍骑马放牧的照片时,高兴地对伯母说,我们的秉建真像个蒙古姑娘了。他们虽然称赞我的行动表现,但在给我的回信中依然不忘提醒我要“切忌骄傲自满起来”,并告诫我“这只是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开始,是革命的开始,青年人革命的道路是长远的,要努力改造世界观,继续前进不停步。”
在阿巴嘎旗插队期间,正是“文革”中最混乱的阶段。整个内蒙古地区由康生做俑而导致的所谓“内人党”问题,及其带来的一系列冤假错案等等,尤其是发生在基层和老百姓当中的许多情况,中央并不了解和掌握。就连我们大队竞有几十户普通牧民家都被诬陷为是“内人党的黑户”,而被称为 “红色好人家” 的只有三户,那些大城市里的逼供信手段也出现在蒙古包里……当伯伯从我的一封封家信中得知这些情况后,立即给予了高度重视,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央就做出了对内蒙古实行军管的“12 .19”决定。客观地讲,在当时那场全国范围内的政治浩劫的严峻现实中,这个决定对遏制内蒙古的极左形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挽救了内蒙古地区当时因冤假错案而遭受厄难的千百万群众,使广大群众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事后,伯母曾在给我的回信里提到:“秉建,你的来信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只不过我的政治敏感性太低,一直没有反应过来,也没有去多想。所以“文革”结束后,内蒙古的许多老干部和老百姓提到此事时,都非常感谢我,可我一直没有把它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很多年之后的1979年,伯母在我结婚的时候,还特意将这件事告诉了我的丈夫拉苏荣。因为伯母知道拉苏荣的父亲就是在“文革”期间的“内人党”冤假错案中被迫害致死的,作为蒙古人的拉苏荣自然对此有着深深的感触。
1970年12月底,我在牧区插队两年半之后应征入伍,和许多青年人一样高高兴兴地走进了解放军这所大学校。由于部队的所在地处于北京市郊区,领导上给我们4个从内蒙古牧区参军的北京知青特批了一天的假期,让我们元旦回家过新年,并要求我们在第二天下午返回部队。于是我们这4个新兵身穿着还没有领章帽徽的新军装,乘坐长途汽车,一路有说有笑地回到了各自的家中。在此之前,因为有纪律不能给家里打电话,所以当我突然回到地处和平里蒋宅口的家中时,妈妈望着日夜思念的小女儿真是又惊又喜,我放下挎包,赶紧跑到楼下的公共电话处,给伯母打了一个电话。
当我兴奋地把这个喜讯告诉伯母的时候,伯母听后平静地说,“你过来一趟吧,这件事你要向你的伯伯当面汇报。”我立刻敏感地想到,糟了!是否二老误以为我当了“后门兵”?怎么会呢,家里长期以来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影响,使我们家的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不可以做任何违反规定的事情,并且处处都很自觉地注意和防止搞特殊化。我在申请入伍时,就专门对招兵的负责人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若属于“后门兵”我是绝对不会参军的。所以一放下电话,我急急忙忙赶往中南海,一路上都在回想着自己参军的整个过程,还真的没想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心情还是比较平静的,甚至感到伯伯和伯母会为我高兴呢。可是,接下来的变化对我来说完全是始料不及的。
进入西花厅时已是掌灯时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伯伯已经站在里院的门口等我了,我高高兴兴地跑上前去向他老人家问好,还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军礼。伯伯一边拉着我的手,一边微笑着问我:“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去?”我愣了一下,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稍做镇定后,我木木的、下意识的、轻轻地回答了一个字“能”。可是我一下子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伯伯立刻看出了我的心态,“我们还是先吃饭吧”,他边说边把我领进了屋里。我默默地跟随伯伯来到客厅,只见客厅一角的饭桌上已经摆好了碗筷。伯母叫我洗手先和他们一起吃饭,其实我已经没有心情吃了。在饭桌前,我只是一言不发,慢慢地往嘴里塞着米粒儿,眼泪也开始忍不住地往下掉。过了一会儿,伯伯开始慢慢地开导我,他说,“你参军虽然合乎手续,但是在内蒙古这么多人里挑上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也不能搞。你要回到草原去,回到贫下中牧身边,继续接受再教育。你应该让贫下中农和工人的子女到部队,把参军的机会让给他们,你在边疆一样嘛。”伯母也在一旁耐心地教育我,她说,你虽然从小就想当兵,但你要知道,还有多少工农子女也非常想参军啊,你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机会让给他们呢?你应该回到草原去,在那里干一辈子革命。看到我在慢慢地点头和思索着,伯伯又进一步启发我:“你不是说大草原辽阔,空气新鲜嘛,我也很想有机会到你们草原去骑一骑马呢,我在以前的战争年代也是骑过马的,我也喜欢骑马啊。”这时候我的情绪已经平静了许多。最后,伯伯要求我回部队后,要主动向部队领导提出自己重返草原接受再教育的申请。尽管有情绪,但我还是答应了伯伯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回到部队后,我立刻向有关领导做了汇报,并且写了书面申请,然后照常参加新兵连的各项训练和活动。
为了继续帮助我转变思想,后来伯伯还让伯母把当时的《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有关介绍天津女知青张勇事迹的文章《壮丽的青春献人民》随同他们的来信一并寄到部队,要我向张勇学习,信中写道:“秉建,你伯伯和我一口气看完后,深受感动。她不仅是你们知识青年应该学习的好榜样,就是我们老年一代也要向她学习。你要回到广阔的草原,再去接受贫下中牧的教育,在三大革命中去接受锻炼,在草原扎根落户,对自己的改造做出优异的成绩,对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接到他们的来信和随信寄来的文章,我认真地学了又学,想了又想,的确从中受到了很大教育,也找到了差距,认识到自己重返草原,继续锻炼和接受再教育是很有必要的,只是心里感到自己没有做错,有很大的委屈。就在接到来信的那天晚上,我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可就是在哭肿了眼睛的同时,我下了决心,要做一名不穿军装的毛主席的好战士。
伯伯一方面做我的思想工作,一方面还亲自找到北京军区的负责同志,要求必须把我退回内蒙古,甚至差一点要为此下命令。就这样,1971年4月初,我重返草原的要求得到了部队的批准,而且就在离开部队之前,我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告别战友离开部队后,我先回到了西花厅,伯伯非常高兴,但还是有些不放心,他问我:“想通了吗?同志。”伯母在旁边说,你听见了吗?你伯伯称你是同志哪!这时的我已经在思想上和情绪上都有了很大转变,痛快地回答:我想通了。可是伯伯却没有放松对我的“敲打”,他特意从百忙之中安排出了时间,在我重返草原之前,专门和我进行了谈话。他十分明确地告诉我,“回去还是要住蒙古包,就和牧民在一起,这一点要百分之百做到”。同时还叮嘱我,“你这次回去以后,对你的照顾可能要大,对你的歧视可能要小,要防止这一点。要坚持在基层,这次回去,可不要再上来哟。”“不会的”,我愉快地接受了伯伯的教诲,把他老人家的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从此以后,我真的开始在各个方面注意锻炼和改变自己了。在重返草原的当天,我就进入西乌珠穆沁旗吉林高勒公社阿拉坦图大队牧民阿匹林瓦的家中,成了他们家里的一个孩子。由于和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在他们的严格教育和热情帮助下,不会就学,不懂就问,很快地渡过了语言关,骑术也有了非常大的提高,掌握并熟悉了牧业劳动方面更多的知识与技能,装束习惯和思想感情都逐渐地牧民化了。可以说,在不长的时间里,我用自己实际的行动得到了牧民乃至远近乡亲们的认可与称赞,也得到了党组织的关怀。1972年的2月,我在自己劳动的生产大队,在草原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国家已经开始实行了以考试、考核、推荐、选拔等方式在知识青年(包括回乡知青)当中,招收工厂的工人,征招部队的新兵,以及招生到大学读书的政策。这些政策在当时为知青们解决了一些出路,很多知青也陆陆续续地离开了农村、牧区、兵团。我们大队、公社,我们锡盟地区也是一样,前前后后走了不少的人。虽然我也被牧民推荐了几次,但我自己从心里没有一点走的想法。
那时我已担任了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和公社团委委员,还是自治区团委的常委。也可能是这个原因吧,1974年春,组织上调我到自治区团委担任宣传部副部长,通知已经到了旗(县)里和公社。但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确实不想走,很希望能够留下来,也愿意继续坚持在基层锻炼。我知道自己是向伯伯做了保证的,应该说话算数才对,但是,我不能无组织无纪律。于是我一方面向组织部门申请留在基层工作,一方面向公社党委表明了自己的决心。公社党委很支持我的行动,并以当地牧民群众和基层党委的名义联名写信给自治区党委,请求把我继续留在基层工作。
为此,我还专程回了一趟北京,把这件事情以及自己的态度向伯伯做了汇报。伯伯赞同我的意见,也很理解我的心情,他要我当面去向自治区的领导做汇报,并强调说:“你一定要讲清楚。不然,人家会说你不服从组织,只听家里的。对这件事情,我们只是作为你的家长,从知识青年的家长角度,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请领导和组织上作参考、作考虑。我们最后还是要服从组织的,所以必须向你们的领导同志讲清楚。你回内蒙古,就去找尤太忠同志,直接向尤太忠书记汇报。”那次我在北京并没有多住,而是很快去了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我按伯伯的要求做了汇报之后就回大队了。不久,自治区党委批准了我本人的申请,也采纳了公社和贫下中牧们的意见,决定同意我继续留在大队,继续接受再教育,继续为贫下中牧服务。
为了让伯伯放心,我更加谦虚谨慎,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但同时也感到了自己的欠缺与不足,我非常想尽最大的努力来提高和充实自己。然而,在还没有解决牧民们实际生活困难的情况下,是很难有条件在不脱产的情况下解决学习问题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上学,进学校读书。
时间过得很快,1975年已经到了我下乡插队的第八个年头。大队里1968年的知青由于进工厂、上大学、当干部已先后陆续地离开,1972年下乡的当地知青和回乡的知青也走了一些。这一年的夏天,一些大学开始派人到基层进行摸底调查,做招生方面的准备工作,他们听说我的情况后,纷纷找到我,动员我上大学。这些学校来自全国各地,有北京的、天津的、上海的,还有其他省区的,也有自治区内的,我谢绝了其他学校老师们的热心推荐,坚持向自治区内的学校报了名,而且是坚持要求学习蒙古语文专业。很多人都奇怪地问我,为什么要学习蒙古语文专业?其实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当然这也得到了伯伯的赞同和支持。
记得我是在“五一”节前后请的探亲假,目的就是去看望伯伯,这时距离伯伯住院快有一年的时间了。我非常想见到他老人家,也想和他多说说话,多讲讲牧区的情况和我们知青的现状。
4月底的北京还没有开始热起来,下了火车,我直奔西花厅。见到伯母后,我的第一句就是问候伯伯的病情,同时要求去看望伯伯。伯母告诉我说,伯伯需要休息和静养,我可以告诉你伯伯你来了的消息,帮你转达你的心情和愿望,但是我不能带你去,这是有规定的。后来我又多次向伯母请求,但是她每次都给我讲,中央对去医院看望伯伯的事情是有严格纪律的,就是她自己去医院也是要按照规定执行的。,最后伯母终于表示,她可以在看望伯伯的时候去和伯伯商量,再把结果告诉我。有一天的晚上,伯母从医院到家里,很认真地对我讲,“伯伯知道你已经回北京探亲了,他很高兴,而且也很想见你,可是我不能带你去医院看望他啊。所以我和你伯伯经过商议,认为可以采取另外一种办法来解决。就是在你伯伯身体允许的条件下,你与伯伯通一次电话。”听了伯母的这些话,我的心里踏实了许多。
由于不知道确切的时间,我每天哪里都不去,就在因伯伯生病住院而清静了的西花厅里焦急地等待着。那几天,客厅里的电话铃声真的让我心中忐忑不安。一天的午后,电话的铃声再一次响起,紧接着伯母就叫我快来接电话,我连忙几步跑到电话机旁。我拿起电话,心情很不平静,有许多话要讲,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先向伯伯问了好,并且告诉他,我很想前去看望他的心情,伯伯说他还好,他也同样想见我。接着,他一一地问起了我的身体、工作和学习的近况。当我向伯伯讲了我想到学校上学,想学习蒙古语文的想法时,伯伯非常支持,他说:“学习蒙古语文的事情我是赞同的。你到内蒙古基层这么长的时间了,怎么还不精通蒙古语文?你和那些懂得蒙古语文的同志不一样,又让你做宣传工作(伯伯还记得上一年自治区团委调我去团委宣传部的事),不会这个本领怎么行呢?学习对工作是有利的,也是为了更好地向群众学习。”伯伯还问到我准备在哪里读书?我回答说,就在内蒙古的蒙语专科学校或是内蒙古大学的蒙古语文专业,伯伯说,那也很好嘛!我正在认真地听着伯伯的话,旁边的伯母却在催我了:“小六啊,你要把话讲得精炼一些,你伯伯他是躺在病床上和你通话的,说话的时间长了,拿话筒的手就抖得厉害。”我只好一边向伯母点头表示知道了,一边还是在恋恋不舍地听着伯伯从话筒里传来的声音:“你要永远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坚持前进,不要后退;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认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感到了伯伯就在我的身边,他慈祥的笑脸就在我的眼前,而且我还能感觉到,伯伯还想跟我说很多的话。但是伯母脸上焦虑的目光,我恋恋不舍地结束了谈话。
当伯母知道了我与伯伯的通话内容后,她也对我的学习愿望给予了热情的支持,伯母特意对我讲了学习的重要性,她说你只有一般的劳动实践还不够,还要有文化、科学知识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才能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才能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伯母还为此表了态,如果组织上和大队的贫下中牧同意你上学,你可以报名,这样做我们没有意见,将来回到基层去工作就是了。
1975年我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了内蒙古大学,成为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新闻专业的一名学生。
作者简介:

周秉建,女,汉族,1952年10月生,北京人,中共党员。1968年8月下乡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插队,曾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团支部书记,公社党委委员,自治区团委委员、常委。1975年9月至1978年7月,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专业读书。是第五届内蒙古自治区人大代表。历任内蒙古锡盟西乌旗团委工作副书记、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文学所副所长、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并挂职任锡林浩特政府副市长。1994年3月至今,任财政部财政监督司财政监察专员、财政部干部教育中心副主任、财政部离退休干部局巡视员。
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