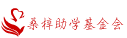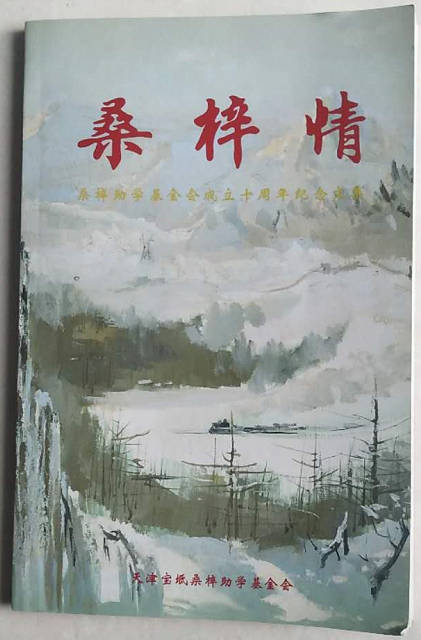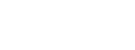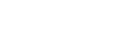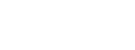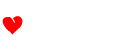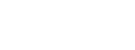伯伯支持我去延安
2014-03-11 阅读:114239次
周秉和

1968年12月22日,是我们那代知识青年难以忘却的日子。 那天《人民日报》套红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的一段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一个震惊中国及世界的疾风迅雷般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此拉开了帷幕。从1969年到1970 年初,全国共有500多万知青奔向了农村。有26000多名北京知青奔赴延安地区插队,我正是其中的一员。从1969年1月到延安至1972年4月离开那里,我历经了人生道路上一段艰难时期。在这时期我经受过插队艰苦劳动的磨练,告别过短暂、紧张的部队生活,重返农村又体验了改造贫瘠荒山战胜困难赢得丰收的喜悦。在3年多的时间里,我有过彷徨、痛苦、迷惘和沮丧,幸运的是我得到了一位伟人,也是我的亲人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教诲和关怀,是亲爱的伯伯在我年轻幼稚的成长时期,帮我不断丢弃那些消极情绪,振奋精神,战胜困难,坚实地迈开了人生的第一步,走过了那段艰难蹉跎的历程。
1968年初冬的一天,学校通知67届初中毕业生可以报名去延安插队。同学们热情很高,有不少人争相前去,也有人鼓动我一起报名,年轻气盛的我当即决定下去插队。事后又犹豫起来,因为当时家境状况很不好,父亲因受迫害在监狱关押,没有生活来源全靠伯伯周恩来接济,如果我能自立,可以适当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但家中兄弟姐妹六人已有五人离开北京在外边工作或插队,仅剩我一个陪妈妈在京,如果我离京家里的事就帮不上了,母亲因压力过大身体欠佳,此时离家是否妥当一时没了主意。这时一个念头冒了出来:何不去找伯伯谈谈想法,于是我拨通了中南海西花厅的电话约定了和伯伯会面的时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伯伯一般很少私人会客, 即使是亲属见面的机会也很少。当伯伯知道我要报名去延安插队的消息后,破例邀我去他那里并和我共进晚餐,可见他很重视这件事情。吃完饭,我提起去延安插队的事,当时心情还有点紧张,我急切地想听听伯伯对此事的看法,只见伯伯沉思片刻,微微抬起头, 用眼睛轻轻地扫了一下我的脸,当俩人的目光相遇时我体验到了一种慈父般的关爱,从伯父赞许的眼神中我已猜到了答案。我清楚的记得伯伯略微提高了一下声调对我说:“插队是你自己定的?好!”然后他笑了起来,会意地和七妈(我们家里都习惯称邓颖超同志为七妈)点了点头, 又一字一句地说:“我们支持你去延安。” 革命战争时期伯伯、七妈随中央红军1935年到达延安,曾经有13年的时间在那里生活,对延安有着很深的印象,每当我提起延安时, 他们便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怀念的感情。伯伯深情地回忆起在战争年代延安老百姓对人民军队的支援最终战胜敌人成立新中国的历史,告诫我一定要继承发扬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 勉励我向贫下中农好好学习,向延安人民学习。伯伯说:“你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陕北农村插队落户,我和你七妈非常高兴。陕北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生活战斗了13年的革命圣地,陕北民风纯朴,群众忠厚善良,陕北的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我已经20多年没有回到过延安了,对那里的情况了解不多了,对你能到那里插队生活,我和你七妈首先是坚决支持。希望你能在那里,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锻炼改造思想,过好思想关、劳动关和生活关,做好生活艰苦和长期落户的心理准备,有困难和问题经常来信,我和你七妈等你的消息。”七妈说:“陕北的生活很艰苦,各方面的物质条件无法与大城市相比,当年我和你伯伯到陕北后,卫生条件差,身穿的衣服里都长了虱子,可我们都管它叫‘革命虫’!你可要做好长‘革命虫’的思想准备(后来我还真的长过‘革命虫’)”。七妈说:“到陕北常来信,你伯伯工作太忙,有困难我来管。你妹妹秉建1968年夏天到内蒙古牧区插队时,我已将家里唯一的半导体收音机送给了她,现在只好给你一些钱,自己去买台收音机,以便在山沟里也能随时了解国家大事,跟上形势发展。”拿着伯父、伯母送给我的插队“礼物”,带着革命前辈的殷切希望,1969年1月9日,刚满17岁的我,满怀热情地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到陕北的第一年, 我来到了离延安县城九十里远的冯庄公社新庄科大队。这里是山区,基本上没有水,劳动和生活条件都比较艰苦。我牢记伯伯、七妈的嘱托,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在农村逐渐闯过了思想关、劳动关、生活关。1970年初, 我从陕北回京探亲,抽空到中南海西花厅, 向伯伯说起自己在延安农村插队的感受, 以及知青工作中的问题,引起伯伯极大的关注。他非常关心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 也想多方面了解延安的情况;于是他要求我能再找一两个插队的知识青年来谈一谈, 同时写一份书面材料。书面材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介绍知青到延安插队的情况;另一部分谈延安当地人民的生活。听到伯伯的意见我心情很不平静,在延安时我们插队知青议论过的问题,现在有机会直接向总理汇报,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我一下子就觉得自己不再是小孩子,真的长大了。我找到曾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何谦同志的女儿何立群, 她当时也在延安县李渠公社插队,是北京八中68届的初中学生,总理对她也很熟悉。当时我们俩都不知道怎么写书面汇报材料,经同何立群商量后,决定把我们所见所闻如实地反映出来。我们认认真真地在一起凑集情况, 我执笔, 她负责抄,忙了整整3天,终于完成了这份汇报材料。
记得汇报是在西花厅伯伯的住所进行的,当时伯伯和七妈都在座。七妈先和我们拉了一会儿家常,问了问何家的情况,并对何立群说:“你妈妈和哥哥的信我都看了,叫妈妈、爸爸不要惦念我们。滨滨(何立群哥哥)的信很有思想, 叫他在部队好好干。”伯伯也问了我妹妹秉建的情况,特别对我们兄妹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十分赞赏。然后就认真地看我们的汇报材料。何立群说我的字写得不好, 七妈说:“字不一定要写得十分漂亮,主要是让人认识。” 伯伯边看材料,边详细地询问了知青和延安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况,我们就把自己的体会、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甚至是牢骚,都一股脑说出来。汇报中我们首先谈起初到延安时的感受,何立群说,火车刚接近西北地区,楼房就看不到了,满眼是高高的黄土坡和稀疏的窑洞。从铜川换汽车到延安,第二天卡车送我们到李家渠公社,贫下中农用马车接我们到高湾大队。刚到队上,晚上没有电灯, 窑洞里很黑,人又累, 有几个女同学居然哭起来了。接着七妈问起知青住的情况, 何立群答道开始是住农民的土窑洞,后来搬进了大队盖的砖窑。她说虽然生活苦,但知青们的适应能力很强,没过几天就熟悉了环境,开始上工了。刚参加劳动,好多同学不会干活,队里给我们记的工分和村里小娃子们一样。七妈问:“怎么小孩也上工?” 立群说那是当地的习惯。她所在的队在延安县算比较富裕的,工值合到一元钱左右。当地娃子一般只念到小学,有的读完三年级就不上学了,参加队里的劳动。男女工分本来就不一样,娃们的工分才是妇女的一半。我也谈到确实有知青和农民、男女之间评分差别大,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存在。还说我在的队比较穷,干一天活工值才有一毛七分钱。伯伯又问我们吃饭怎么样。何立群说最初是队里派人做,以后就自己学着做。开始不会烧柴,饭总是做不熟,慢慢地就都学会了, 还会贴饼子,做高粱米饭。伯伯笑笑说:“好!好!你们学会了独立生活,也学会了克服困难。青年人只有经过实际锻炼才能挑起革命重担。”听到伯伯的夸奖,我们兴奋起来,争相表白一年中下乡锻炼的成果。我主要谈了我们克服生活上的困难,学会农业劳动的过程。我说,刚去时分住在老乡家里, 后来搬到新建的窑洞,由于新窑潮气很大,不少知青身上长了疮,有的还化了脓,又疼又痒。当时粮食不够吃,在配给的粮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黄豆,知识青年在北京吃惯了大米、白面,一时不能适应陕北农村的饮食,常常出现拉肚子、消化不良的情况;从劳动强度看,搞基建,拉石头,运送粪,掏羊圈等比较重的活都压给了知识青年,知青干劲很足,没有多久各种各样的农活都会干了,而且大部分知青干活不偷懒,上进心很强。何立群接下来给伯伯和七妈举了两个例子, 说明知青不怕吃苦甘于奋斗的精神。一个是上山收麦子, 突然下起雨来,山路又窄又陡,路滑很难走,要在北京晴天都不敢走,可那天三个女知青硬和社员们一样,背着麦捆走下山,浑身都湿透了。另一个事儿是她们上延安参观,来回要走50里路, 她们不忘队里的生产,特意推上粪车为队里带回一车粪。伯伯和七妈听了连连点头,赞许我们锻炼了本领,也锻炼了意志。伯伯还非常详细地询问了知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根据自己所在队里的情况和平时知青常反映的情况,向伯伯作了汇报。何立群告诉伯伯,最主要的问题是知青生病后无人照应,只能自己照管自己。女八中高一的一名女生,因患斑疹伤寒,高烧不退,知青们赶了几十里路送她到延安县医院,住院后又轮流看护她直到病好;还有一个女生因发山洪淹死了,当时水不深,只是身边没人,死后很久才被发现。 伯伯听后连连说:“怎么会这样?可惜了!”我谈到男知青因做不熟饭,油水少吃不饱,管不住自己,打架闹事,有的还偷东西。被发现了, 当地人就用土方法审问偷东西的人,把他绑起来,连唬带吓让他承认错误。我们还谈到有些生产队对知青关心不够,知青吃住的问题没能很好解决,知青思想比较混乱等问题。伯伯很关切地问起公社和县里有无派人来队里管理知青。当我们告诉他不是每个队都有时,他沉静了片刻。随后我们谈起延安百姓的生活,伯伯问起当地农民种些什么庄稼?有没有副业?我回答说,当地农民主要种的是糜子、高粱、小麦, 但许多地方收成不高, 我所在的生产队因为交通不便,所以副业很少, 只是私人养点猪、羊、鸡。何立群说,她们队位置好一些,在马路边上,队里有许多副业,马车拉煤往延安城送,地边河滩上种蔬菜和西瓜,吃不了就卖出去,妇女儿童为修公路砸石子也可以赚点钱。伯伯点头说:“那你们队的农民生活要好得多。”
谈到陕北人民,我们告诉伯伯和七妈,那里虽然穷,但人民热情淳朴,有乐观精神。他们像对待亲生孩子那样教我们生活。逢年过节还请我们到家里吃饭,最好的饭就是羊肉胡萝卜馅的饺子。我们和青年农民交往多,他们业余时间也和我们议论国家大事。公社演电影,他们带我们走十几里地去看,电影散后大家结伴而行,他们打着手电领路,有说有笑,这种乐观情绪给了我们安心插队的精神力量。伯伯和七妈听到这里都欣慰地笑了。我们也如实地谈起有的农民生活很苦,穿的大多是自织的粗布衣,而且十分破旧,有的小孩还穿不上衣服, 全家几口人盖一床被子。有的老乡家里还在吃糠, 还有教育水平低,文盲多,买卖婚姻严重,姑娘出嫁要称体重……当我们说到农民吃糠、延安城里要饭的人很多时,伯伯脸色很不好,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解放这么多年了,还这样?我都不知道呀!”当时我们正年轻,并不真正理解伯伯忧国忧民的心情。事后曾听伯伯身边的工作人员张树迎叔叔说,伯伯那些天心情一直都很沉重。
后来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 伯伯还专门提到这件事:“延安的问题这么多,大人没反映,孩子反映了……不能只建设西安,要考虑延安……” “陕北人民哺育了我们,全国解放二十多年了,一些群众生活还这样困难?我心里非常难过。”那天谈话中,我们见伯伯心情沉重,就忙岔开了话题。何立群谈起延河水的秀丽壮观,平日里清亮见底缓缓地流,到了秋季, 上游水下来,水位猛涨,波涛滚滚,场面极壮观。我还说我们参观枣园、杨家岭的观感。这引起了伯伯对当年的回忆,伯伯说:“1939年延安城里被日寇炸得很烂,但分散在城外的几个地方都是很不错的。”七妈说:“桥儿沟天主教堂那不是挖了许多窑洞, 咱们鲁迅艺术学院就在那儿嘛,桥儿沟河对面柳树沟是和平医院, 新华社、抗大在宝塔山对面的清凉山下。”伯伯还问了枣园、毛主席旧居的情况及抗大校址。我说都保护得挺好。伯伯和七妈都感慨地说离开延安那么多年了,真想回去看看。3年之后,伯伯拖着病体陪同外宾回到了延安,完成了他老人家想看望老区人民的宿愿。
那天中午我们和伯伯、七妈一起吃了饭。虽然只有面条和几样小菜,我们却吃得格外香。吃饭时,我们还在谈延安,伯伯又问了我们许多问题,比如延安当地农民养羊的多不多,羊毛是不是自产的,劳动用什么工具, 人口多不多, 有没有种树等等,我们就所知道的都一一做了回答。那天吃饭快结束时,伯伯对我们说:“你们谈的情况,虽然是个很小的面,能不能代表整个延安地区的情况我还要了解。但是你们谈的有些问题,我看会引起中央的重视,不仅中央会重视,陕北也会重视的。”吃过饭,伯伯有公务要走,临行前叮嘱我,要坚持回延安插队。我向他作了保证。不久,我们就回延安参加当地春耕了。4月在延安的知青们就被传达的一条重要消息所振奋——1970年3月10日由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会议由周总理亲自主持,参加会议的有陕西省及延安地区的主要领导和知青办的负责人,还有北京市领导和中央部委有关单位。总理在会议一开始时提到,是因为有几个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向他反映了延安的现状和知青上山下乡中所发生的一些情况,感到问题很严重,有必要召集有关同志来京了解更详实全面的情况,共同商讨如何解决北京知青插队落户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以保障上山下乡运动的正常发展,我暗自为能对知青问题的解决做出微薄贡献而高兴。
后来听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回延安传达精神时说,总理仔细听取了延安各方面同志的汇报后,他为延安的落后状况、人民生活的困苦而落了泪。他说解放这么多年了,延安人民却还在吃糠咽菜、生活艰难,我当总理的有责任,对延安关注的不够,对不起延安人民。在座谈会上总理亲自带领大家和他一起重温了毛主席在1949年给延安人民的《复电》。《复电》号召延安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扬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儿,那么一种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延安建设好。伯伯还指示北京市有关单位对口支援延安,并派出大批北京干部到延安直接深入北京插队知青落户的生产队,协调地方具体解决知青们的各种困难,从思想上,生活上,劳动分配上给予帮助和支持。会议还做出了严历打击各种破害知青上山下乡的行为和犯罪活动,使北京知青们感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插队同学们的情绪逐步趋向稳定。
在伯伯,七妈的关心下,我从北京又回到陕北继续我的插队生活。回延安后,我调到枣园插队,这里曾是毛主席和伯伯等老一辈革命家生活战斗过的村子,条件相对好一点。我给七妈写信说这里的同学搞的是30来人的集体大灶,每人每月要交5元钱的伙食补贴费,七妈就让秘书赵炜同志每月给我寄5元钱,我赶紧又说这还差点,还要点卫生和学习(如报纸和书)的费用,七妈就又加了3元钱,每月给我寄8元钱的生活费,既支持了我的基本生活需要,又防止我比其他同学宽裕而滋生不良习惯和大手大脚。伯伯和七妈对晚辈的严格教育从我们很小时就开始了,不许我们搞特殊化,不许亲属打着他们的招牌提要求、要照顾和走后门,他们要求我们对外人不要提及与他们的亲属关系,更不能在他们的对外活动中出头露面。他们要求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就是老百姓,普通群众一个,要老实做人,老实做事,老实生活。他们的待遇是党和国家订的,是工作需要,晚辈无权提特殊要求,而他们生活的简朴,对人民群众的关爱和平易近人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1970年的夏天,七妈因公务回延安,这是她老人家自从1947年离开延安直至1992年去世,唯一的一次回延安。她这一次的行程没有声张和宣传,其间她还特意到枣园参观了毛主席当年讲演“为人民服务”时所站的讲台,而我当时正在离讲台不远的地方干农活,对七妈的到来一点儿都不知情,收工吃晚饭时,才从碰见过七妈的同学们的交谈中得知此事。虽然感到遗憾,但我心中非常理解七妈她老人家的用意:明知侄子就在这个村插队,就是不向人提起,以免大家都知道我有这层关系而得到特殊关照,还会影响我的锻炼成长。恰恰村里陪同七妈参观的人也没向她提起我,等于从侧面向七妈证实,我在枣园没有泄露与伯伯、七妈的这层关系,并没有搞特殊化,遵守了对他们的承诺。
1970年底,新疆军区到陕北招兵,这被知青们当作既能脱离农村又有前途的改变人生命运的大好机遇,大家踊跃报名,而枣园村只有我是唯一体检合格的人,没有犹豫我满怀激情身着军装踏上了新的征程。1971年初,经过3天闷罐火车和7天带篷卡车的漫长征途,我到达了新疆南疆军区目的地。刚到驻地,我赶忙给伯伯、七妈写信汇报,内容大意是向他们报告个好消息:说我参军了,将在解放军这座革命大熔炉里炼就红心,为保卫祖国站好岗、放好哨。另外请七妈不需再向陕北农村汇生活费了,随信还寄去了我的军装照片。正当我努力训练力求以优异成绩结束新兵连的生活时,收到七妈的来信,这是一封犹如巨雷轰顶的来信,七妈在信中说:“秉和,接到你的来信得知你已经参加解放军,我们当然也很高兴,但是你伯伯专门查阅了国家征兵的有关政策,凡父母正在受审查的子女,不可参军,你的父亲现正接受审查(父亲周同宇受江青一伙迫害从1968年至1975年被关押7年,1979年平反。)所以你的情况属于不符合入伍政策,既然违反了政策,就应改正。你伯伯已经向送你参军的陕西省和军区领导交待了,让他们派人去接你,还与新疆军区领导联系了,让他们放你回去,你要作好思想准备,脱去军装复员,继续回陕北插队当农民。”伯伯、七妈了解我刚刚当了3个月的兵,突然送回农村插队对我打击会很大,所以一再提醒我要有思想准备,但我的抵触情绪仍然很大,就我个人在山沟当农民和边疆当战士的实际感受中,认为到军队和去农村有着天壤之别,在农村一个月才吃上一顿白面馒头或面条,其它都是很难吃的杂粮,况且还吃不饱;在边疆军营,每天三顿都是白面米饭。在农村起早贪黑干农活累得要死;在部队跑步出操回营房就开饭,不用像农村自己砍柴生火做饭再出工;上午军队练拼刺、打靶虽然有点累,但与农村的重体力劳动无法相比,下午开会学习搞批判属正常活动,在农村学习耽误的生产时间就要自己补上。当农民前途渺茫不知前景如何;当战士可以提干,复员后国家还安排正式工作。想来想去、比来比去,越想越沮丧,一句话,当时让我回农村真是想不通!冷静一段时间后重读来信,我才慢慢地想通了。七妈说:“秉和,你要坚强,想开些,还有那么多的知青不是都在农村当农民吗?对你的困难伯伯和七妈继续帮助解决,但违反政策的事一定要改正,这是我和你伯伯对你最起码的要求……”我必须得想得开,伯伯、七妈对我们的严格要求从小就习惯了,当时又是“文革”非常时期,伯伯的日子很不好过,“文化大革命”将他置于极其艰难的处境,更有人在他背后捣鬼整他的黑材料,连我父亲那么老实规矩的人也要整,就是想通过整我父亲整出对伯伯不利的局面,甚至整垮伯伯,搞得伯伯不得不向中央作检查他有一个“有政治问题”的弟弟。我很难,但后来才知道伯伯比我难处更大,我这点难根本就没法同他比。我很庆幸最终战胜自我执行了伯伯的安排,回到陕北插队。若干年后当我人到中年,和同年插队知青们一起谈到我因不符合征兵政策而被周总理“走关系”将我从部队弄回农村的“事件”时,感悟到另一层意思:毛主席号召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周总理必须忠实贯彻执行,可如果他最亲近的两个后代亲属都离开了农村(还有我妹妹周秉建,也是1971年从内蒙古牧区插队点出来当兵,并于当年春季新兵连队训练结束后又返回内蒙古牧区继续当牧民去了),伯伯再动员其他同志送子女上山下乡就会缺乏说服力。虽然这只是一种猜想,但我们兄弟姐妹都坚信一点,那就是凡是伯伯、七妈要求我们做的,肯定是对的。即便有些事当时想不通,也是因为我们有局限性并且不成熟。先按他的安排办,以后迟早会明白。伯伯安排我们做的事,肯定是经过他老人家深思熟虑的,是对我们负责的,更是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的,是对我们亲属的严格要求。既然命运有幸让我们成了他老人家的侄儿,那么付出一定的代价也是理所当然的,必不可少的。这代价就是我们只能比别人磨难更多,要求更严,生活更艰苦,工作更努力,牺牲和奉献更大,而个人得到的比别人更少。因为我的伯伯本人就已经将自己的全部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的事业,献给了他热爱的国家和人民。
1971年4月,当我按照伯伯的要求从部队重返延安后,很多人也就知道了我同伯伯的这层关系,知道总理有个侄子曾在延安插队后当兵现在又被送回来了。上级领导为使我继续安心插队不受干扰,防止我与伯伯的亲属关系被周围的人知道后会影响我的正常插队生活,因此安排将我调到了延安县的另一个公社——河庄坪公社落户。为了保密,领导还建议我另起一个名字。我一想,那就踏踏实实地在这干吧!于是我就给自己另起一个听起很革命,叫起来很响亮的名字——周志延。志在延安,好让伯伯和七妈老两口放心。由于刚刚从环境较好的部队回到条件艰苦的陕北农村,伙食相差很远,干农活体力消耗很大,我的身体一时适应不了这些巨大变化,加上心情不佳,刚刚下农田干了三天活我就累病了,连续发烧作恶梦、吐鲜血,后来就昏迷了。幸亏新落户村(石窑村)的知青同学和老乡们发现后用驴车将我连夜送到延安城里的医院,住院打针吃药治疗很多天才好。医生说是大叶性肺炎,如治疗不及时再晚点儿送来有生命危险。病好回村后,队里给我分配了一个轻体力活的工作(在电磨坊里磨面碾米,这还是原先干这活的一位女知青同学主动给我让出来的,她自己则去田里干累活去了,这件事我至今都非常感激她!)才使我的身体慢慢恢复起来。我在医院给伯伯、七妈写信汇报:我又回陕北农村落户了,换了个村,改了名,就是身体不济生了病,但现在已稍好,请二老放心。但二老看来是见到我的来信并不放心,他们肯定是从我的来信中察觉到了我的情绪不太好,从部队回农村对我的打击不会很快恢复过来,我的病情也让二老惦念,于是七妈亲自操笔(平时大都由她口述秘书赵炜阿姨代笔)给我回信,她在信中说:“志延,你的名字取得很好!顾名思义你是志在延安,志在延安农村。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三大革命中锻炼成长,那是有多么深远的意义呀!再说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全世界人民向往的地方,你在这样的地方参加革命和建设也就是全国革命和建设的一部分,如有所贡献也就是对祖国和世界革命做出贡献啊!但却不要骄傲才好。你能服从命令,按照毛主席教导青年们应走的方向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力争坚持下去,就是好样的青年!伯伯和我觉得能有你这样的侄儿和小六侄女(她已回去原地区另一队插队了)而非常高兴!你在医院来的信已收到,不知你是否病好?病后身体怎样?我们都在惦着。希望你接信后先来一信告之,以慰我念……。希望你能够像去年回京探亲时向我说的那样以后好好干,更重要的是要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做一个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青年!祝你不断进步!七妈手书1971年5月6日。”手捧七妈的来信,更加深感二老对我延安插队之事是多么的重视,多大的支持和期盼,我的责任有多重。没说的,干吧!不是全国还有那么多的知青都还在或正在陆续奔赴农村的广阔天地去战天斗地吗?与大多数比我家庭和个人困难更大的知青相比,有伯伯和七妈二老的全力支持我实在是太应该知足了。至此,我暗下决心一定在农村拜农民为师,刻苦锻炼,积极参加劳动生产,为延安面貌做出自己的贡献。
1972年插队生活进入第四年,此时国家政治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9•13”林彪事件后,国内的混乱局面有所好转,中美关系大门开始打开,工农业生产有所发展,一批老干部开始恢复工作,政治形势趋向平缓。虽然还远远没有能达到局面的根本好转,但是全国范围开始了大规模招收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我听说招生政策里有规定:“可教育好的子女”(既父母正接受审查或出身不好,但本人表现较好的孩子)也允许上学。经过贫下中农推荐,领导批准,我于1972年4月进入清华大学,学自动化专业。5月的一个星期天,离别北京3年后,在中南海西花厅又一次见到了日夜思念的伯伯,第一眼给我的印象是他老人家变老了,面容显得消瘦,但精神还是那么好,眼睛依然那么炯炯有神。他问我:“秉和,你这次上大学在家庭出身上虽然符合政策,但是有没有走什么门路呢?”我说是贫下中农推荐,招生单位审核批准,正规录取上的大学,绝对没有走门路,伯伯放心地笑了。但是接下来伯伯又问我:“你想没想过毕业后还回陕北继续为延安的建设工作呢?”我可真没思想准备,有点发蒙,回答说我学习的专业在延安没有对口单位。伯伯思索了一下说:“是呀,如果能学习水利的话就对口了,延安的水利化建设还是很需要的,清华正好有这个专业,我想是不是跟你们学校领导协商一下,给你转到水利专业学习。”因为当时伯伯工作太多,话没谈完就走了,后来我又曾到伯伯处去看望他,伯伯没有再提起转专业的事,我猜想其原因可能有几点,其一是如果专门给我转专业,这反而倒成“走门路”了;其二是当时的清华、北大正在江青的爪牙迟群、谢静宜的严密控制中,与他们协商肯定会“无事生非”,说不准什么时间会被他们用作整人的材料。尽管伯伯一直在与他们作斗争,但迟、谢等人还是在我上学不久就在江青的指使下搞起了“反击右倾回潮”的运动,此后又借“批林批孔”、“评水浒”等运动将其罪恶矛头直指敬爱的伯伯,把清华、北大办成了反周总理的据点,学习的任务都被各种运动搞乱了,我们学生是什么也学不好,转学什么专业也没用了。
1973年夏季,越南国家领导人访问中国,其间伯伯曾陪同他们访问了延安。伯伯一行到延安,延安沸腾了,延安人民热烈迎接阔别延安20多年的周总理,所到之处人山人海。总理非常关心延安的生产建设,关注革命老区人民的生活,再次为延安的落后状况和人民生活的艰辛流下了热泪。他与当地领导一起研究改变延安落后状况发展生产的计划,与当年认识的老乡了解情况唠家常,发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当时还住在延安的知青同学给我传回一个消息:总理一行回访枣园时,枣园村支书雷治富领着村民们热情地欢迎他老人家,在热烈而亲切的交谈中,总理忽然问雷支书:你们是怎么让周秉和上的大学?他走没走后门呀?雷支书回答说:娃娃在我们这里表现很好,是贫下中农推荐他上的大学,不是走后门。总理又问:那他毕业后还回延安来参加延安的建设你们欢迎不欢迎?雷支书回答:我们当然热烈欢迎!伯伯回京后不久很快将我召到西花厅,他认真地告诉我:“我已经和延安的乡亲们说好了,等你大学毕业后还回延安继续参加延安的建设,那里的人们可都说欢迎你回去呢!”就这样,我又作了第二次回陕北的思想准备。两年后,在我临毕业的1975年,伯伯的病情已经很重,我们兄弟姐妹也不被准许去医院看望他老人家,而“四人帮”却越发猖獗,他们先批判了教育部长周荣鑫,又将矛头指向了邓小平同志。1976年1月8日,敬爱的伯伯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所热爱并为之奋斗奉献了一生的国家和人民,而“四人帮”却还要批“党内最大走资派的黑后台”,罪恶的矛头直指已经去世的伯伯。面对“四人帮”的嚣张气焰我心中十分气愤!个人虽然没有抵抗这帮恶势力的能量,但对形势的发展很不放心,一边留心着“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一边又暗暗地为去世的伯伯祈祷。时年10月“四人帮”垮台后,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变,由于要照顾半身不遂刚出狱的父亲,我留在了北京。现在回想起伯伯生前期待我回延安的嘱托,心里十分愧疚,深感对不起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
岁月如梭,现在我们这代当年的“老三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都早已是年近花甲之人了,回首往事,追忆当年伯伯和七妈在我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期间乃其前后对我的关怀教育和殷切期望,心中充满感激之情。感激他们二老对我们亲属的严格要求和亲切爱护,庆幸能在他们身边亲身感受二位老人的精神风采和人格魅力,他们崇高的品质和情操永远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楷模,有幸在他们身边生活并接受教诲,是我一生的幸福。
作者简介:

1969年1月9日到延安县冯庄公社新庄科大队插队. 1972年4月进入清华大学,学自动化专业.毕业后在北京市自动化技术研究所、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等任职
相关内容: